无论如何,一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于是我考虑起了另一个可能性:我们全家在尼泊尔团聚。
按照我的想法,我可以先去尼泊尔,尼泊尔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在当地找个中介将旅游签证转换成商务签或者学生签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假如有了尼泊尔的长期签证,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全家不妨先定居在尼泊尔。印度和尼泊尔之间是开放边界,我太太作为印度公民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就能在尼泊尔居留;我儿子有印度的出生证,也可以暂时在尼泊尔冒充一下印度公民,谁会去调查这么小的小孩呢?
我是个惯于漂泊四海的人,过去一个人的时候,家对我而言就像一个工作的场所,在哪里都无所谓;如今有了妻儿之后,依然觉得家安在哪里不重要,简陋或豪华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齐在一起。只要跟家人在一起,无论是定居在南印度还是尼泊尔还是中国,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印的政治博弈导致了这样一种荒诞的局面:印度的家容不下我,中国的家容不下我太太,可难道天下之大还会无处容身吗?生活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之中固然抉择有限举步维艰,但只要能够跳出这个夹缝,顿时海阔天空。
于是我们就开始兴冲冲地制定起了举家搬去尼泊尔的计划——我先过去落脚,搞好签证租好房子之后,再让我太太和馒头过来。当然,也不能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性——我拿不到尼泊尔的长期签证,只能用旅游签证在那里呆90天。如果真那样的话,也只好认命了,到时候再作其它打算,毕竟谁知道三个月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定下了计划之后,首先要搞定的就是尼泊尔签证。
很多这两年没有出国的人可能不知道,疫情开始之后许多原来可以落地签的国家都暂停了落地签政策;不过随着全球疫情的缓和,一些国家又陆陆续续有条件开放了落地签,尤其是那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尼泊尔便是开放得比较早的国家,从2021年9月份开始持有疫苗接种证明的话可以办理落地签,入境后也不需要隔离。
我是印度第一批接种疫苗的,4月初就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也正是由于我接种得太早了,当时并没有拿到接种证明,因此我需要提前办好尼泊尔的贴纸签证。办理尼泊尔签证很容易,填好在线的签证申请表格将护照等材料送去尼泊尔大使馆一天就能出签,并不需要本人前往,且中国公民免签证费。
由于我的护照带在身上,9月28号那天我的太太和基友为此开车来了一趟集中营取护照,顺便帮我送来了一大堆补给品。我刚进集中营的时候就跟阿茂说:假如一个星期内我出不去,那么我多半得在这儿呆一个月。彼时我已在集中营里关了两个星期,必须为接下去的持久战做好准备,来自家中的补给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有了床单枕头这些东西,我才感觉自己睡上了一个真正的觉;而运动鞋和跳绳让我又能开始有氧训练。
他们过来一趟十分辛苦,从我家到集中营220公里要开5个小时。由于带着馒头不方便在外面过夜,他们计划当天往返,早上5点便出发了,10点多到了集中营。
我前面说过集中营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铁门之间是办公室行政区,会客的地方则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铁门之间,探访时间为朝九晚五。据说在疫情之前,访客能进入到集中营里面,牢房门一关还能过个夫妻生活啥的;我在这边的时候,只见到有小孩子进来过,夫妻生活是别想了。
虽然伊利安的越狱进一步导致了这边管理的严格,但探视的时候依然完全有机会把一些东西夹带进来——看守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我太太带给我的两个纸箱,并不会搜查随身物品;会面的时候也没看守在边上盯梢,只要不是太大的东西很容易就能夹带进来。我让我太太把我自己的电话卡带给了我以便接收各种验证码,见面了才发现她其实完全可以把我原来的手机带给我,往裤兜里一塞就行了。
那时馒头的水痘差不多已经好了,脸上还有最后一两个血痂没有脱落。作为一个不到10个月大的孩子,依然跟我走时一样懵懂无知,见到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心想,如果我现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大概完全不会记得曾有这样一个爸爸;而假如我跟他分隔一年半载的话,再见的时候恐怕都不会认得我。
我之前在那篇《【印度日记】疫苗有时,归期无期——印度疫苗接种记》文章里提到过一位娶了藏南媳妇的兄弟,他2020年6月回国的时候,孩子只有七八个月大;2021年7月他好不容易拿到签证回到印度时,孩子走路已经走得很好,却并不认识他——虽然现在的通讯极为便利,可视频通话毕竟替代不了膝下的承欢……这样的事情在疫情期间十分常见,但我绝不希望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太太在探视我的时候反而显得有些拘束,该说的早已在电话上聊过。看到集中营的环境让我太太颇感焦虑,有些坐立难安。
倒是我基友过来比较有用一些,他能用泰米尔语直接与当地人沟通,在跟办公室里一个Q Branch的小领导聊了之后,获得了一些信息。
那个小领导说这个集中营只是一个负责拘押的地方,这里面关着的有些是法院的人,有些是CCB(Central Crime Branch)的人,有些是Q Branch的人,构成很复杂。而我则属于金奈移民局的人,我是他们抓进来的人,所以只有他们能放我,建议我们直接去找移民局谈。
我基友之前也尝试过给移民局打电话,他没有我太太那种坚持不懈死缠烂打的精神,几次打不通便放弃了。尽管他已经跟邦政府秘书聊过,但他还是很希望能跟移民局官员面对面交谈,以便能够搞清楚他们真实的想法。于是离开集中营之后,他们临时决定改变计划,直接从崔奇驱车5个小时杀去了金奈,到移民局讨一个说法。
此行金奈一路食宿交通种种这里就不赘述了,他们这趟对移民局的突袭却并不顺利,移民局官员拒不接待他们,理由是没有预约过——毫无疑问这只是移民局的刁难,或许是由于之前我太太在电话上跟他们争执过。
然而我太太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她打出一手苦情牌,抱着馒头在移民局的前台哭着要求见这里的负责人。移民局里面有一个小官员心生恻隐,给她指了条路,教她赶紧在手机上现写一个邮件预约。
提交了预约之后是无尽的等待,从早上10点一直等到下午5点,最后在他们临下班之前,才终于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我太太试图解释和说明,然而那个负责人却粗暴地打断了她,根本不允许她说话,只让她把一切都写在纸上之后便打发她走了。没人知道他后来究竟有没有看过这张纸,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那次移民局之行无功而返。
那天移民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我基友由于等在外面,对当天的事情也是一头雾水。而我太太从移民局回来之后就陷入了抑郁,整个人十分消沉,什么都不肯说。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段黑暗、丢人、永远不想再提起的挫败。
我太太那天的经历虽然我不曾亲见,她也不愿多说,但大抵可以通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来猜想:一个失去了依靠的女人带着九个月大的孩子坐了10个小时的车上访,想要为自己男人讨个说法,却在无情的官僚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
那几天大概是我太太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后来让她终于渐渐振作起来,正是因为后来着手落实去尼泊尔的计划。
我并不完全确定自己能不能去尼泊尔。印度政府拘捕我的那个命令上写的是把我关在集中营里直到我离境为止,并没有限制我去哪里。但皮特却说我只能够回中国,这里的人是不允许去第三国的,要走遣返流程。
我有点不信邪,觉得自己跟他们这些有案件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护照都早就被警察收走了;而我有护照和离境许可,应该只要离境就行了,离开印度他们凭啥管我去哪儿?我那会儿忘了印度是一个“三不讲”国家——不讲逻辑,不讲信用,不讲道理。
出于保险起见,在东航航班被取消之后,我就写过邮件给了移民局,出示了航班取消的证明,问他们我是否能够改买去尼泊尔的机票离境。移民局的回复既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只是说让我申请新的离境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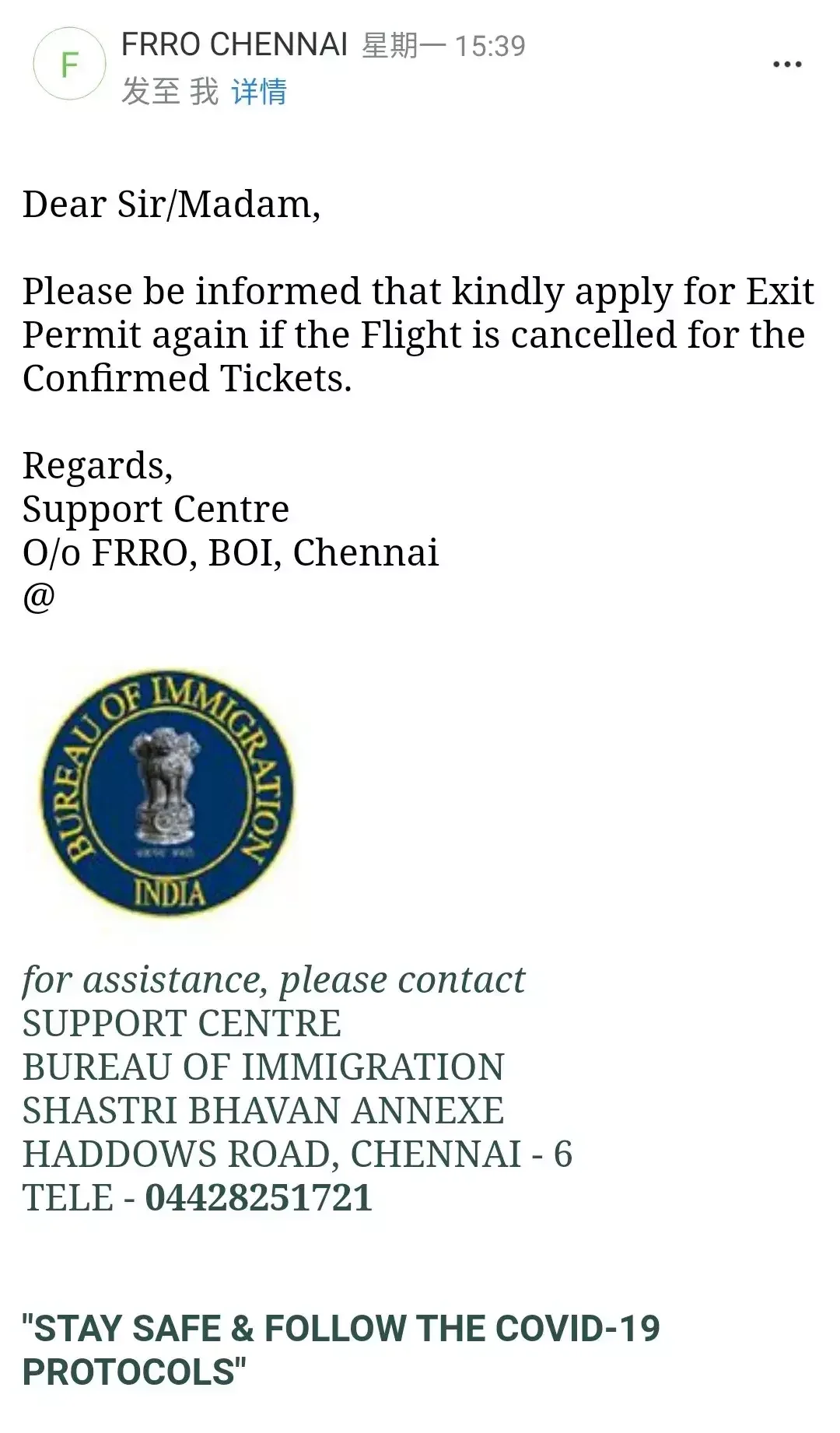
我们把这一回复当做了移民局的默许,考虑到把我护照寄到德里去办完签证再寄回来需要时间,移民局批复离境许可也需要时间,因此我们订的是两个星期后的10月18号去尼泊尔的机票。
确定了去尼泊尔之后的那几天是很令人振奋的——开始倒计时离开集中营的日子,忙着联系尼泊尔的朋友,在爱彼迎上查找可以长租的房源,讨论究竟是要定居在加德满都还是博卡拉,盘算着去EBC徒步,幻想着接下去在尼泊尔的美好生活……